目录
快速导航-
特别推荐 | 黄河源传(节选)
特别推荐 | 黄河源传(节选)
-
特别推荐 | 佛光普照
特别推荐 | 佛光普照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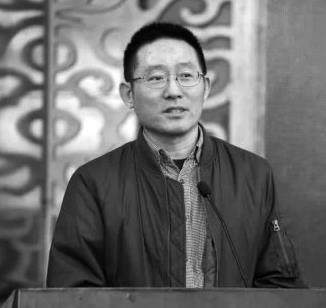
特约专栏 | 开会记趣
特约专栏 | 开会记趣
-
作家视野 | 文余琐记
作家视野 | 文余琐记
-
作家视野 | 供春回家
作家视野 | 供春回家
-
作家视野 | 万物有相
作家视野 | 万物有相
-
作家视野 | 黑夜拥有寂寞和歌声
作家视野 | 黑夜拥有寂寞和歌声
-
别具只眼 | 南京知青
别具只眼 | 南京知青
-
别具只眼 | 放猪记
别具只眼 | 放猪记
-
别具只眼 | 山有木兮木有枝
别具只眼 | 山有木兮木有枝
-
别具只眼 | 巴山南北
别具只眼 | 巴山南北
-
人与自然 | 文冠当庭
人与自然 | 文冠当庭
-
人与自然 | 九章海
人与自然 | 九章海
-
散文新星 | 清洁女工笔记
散文新星 | 清洁女工笔记
-
散文新星 | 东埝上
散文新星 | 东埝上
-
海天片羽 | 附着者
海天片羽 | 附着者
-
海天片羽 | 春节
海天片羽 | 春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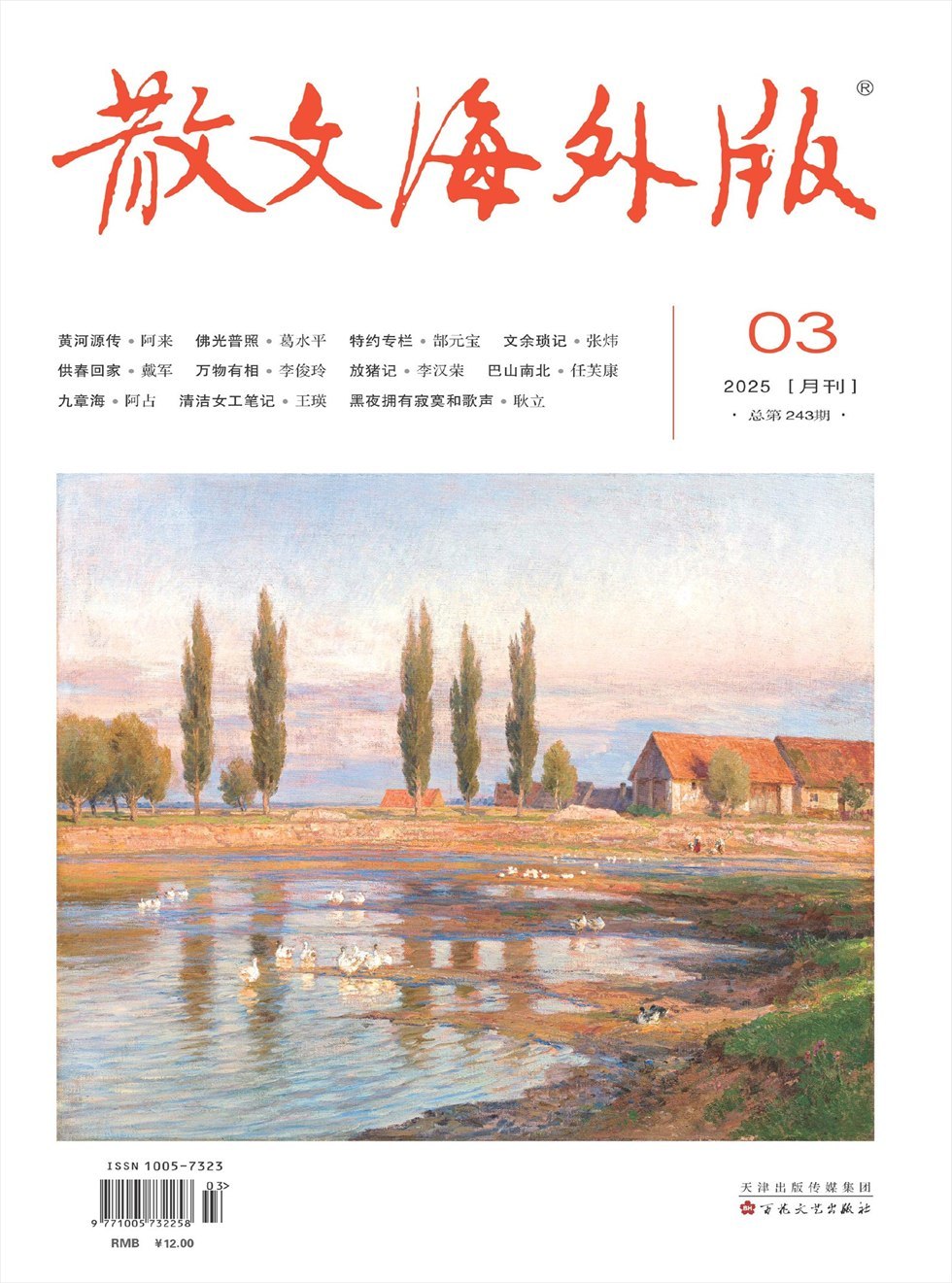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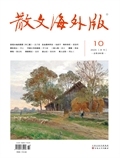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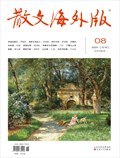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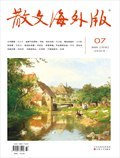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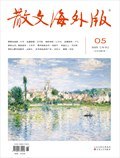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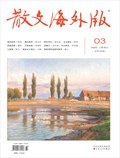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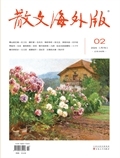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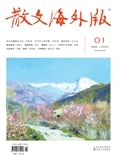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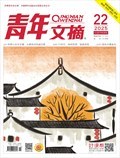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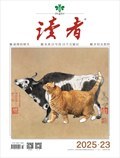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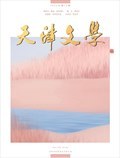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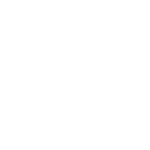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